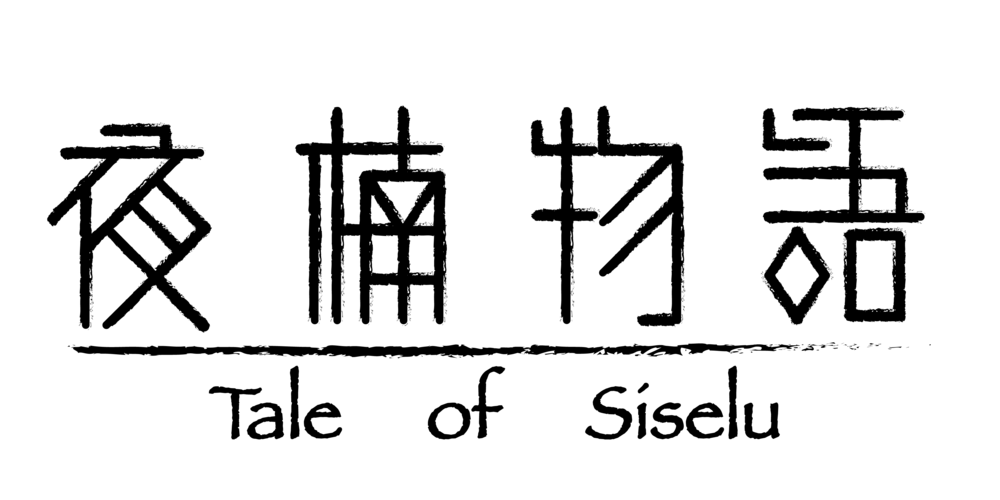我記得,在寒風凜冽的北方大地,除了一片白茫,只有讓人倍感孤寂的北風呼嘯聲;當隆隆的砲擊聲以及魔法爆破時的悲鳴響起時,才會驅散孤寂的冷風,除了白以外的顏色,就只有戰士們涔涔的鮮血,在純白的大地開綻著一朵又一朵的豔紅鮮花。
「通訊兵!傳令給第三班和第四班,在第二波的佯攻之後,直接往樹林後撤;第五班跟第六班,你們在樹林前埋好引雷,等我們的弟兄撤退進來之後,拖著那些追擊的敵軍;第一班跟第二班,任務不變,把火點起來,砲台的魔素迴路解凍後就開砲餵飽那些紅軍,讓他們這群只敢窩在後方的娘們瞧瞧大和帝國的誠意!」一道鮮血從發號施令的黑髮青年軍官額頭上流下,浸紅了軍官的眼眶和臉龐,但他依舊面無懼色地指揮著。疲憊的軍士看見佐藤奮勇指揮的模樣後,也吆喝著,再次提振起精神進行手邊的工作。
「佐藤大尉,任務已傳達下去,不過營本部那裡依舊沒有回應,一連以及三連的人目前還是聯絡不上。」
「狀況我知道了。」
「報告大尉,這樣再撐下去實在……」
「我知道。我們的任務是掩護前鋒部隊順利撤回,如果在這裡我們就直接撤退,一、三連的弟兄們就會全數被圍,只會被殲滅殆盡。」
「但是……」
「我們的兄弟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強悍,就算他們被切斷通訊,也不是那種輕易待斃的戰士。只要撐到日落,對方就一定會撤軍,就算是紅軍,也不敢正面面對羅莎莉亞夜晚的暴雪。只要守住這塊高地,就能讓其他連也順利撤退,我們要為我們的兄弟、為大和帝國堅守這塊陣地。」
「是!大尉!」
如果一切如自己所想就好了,佐藤心想,大吾、學長,你們可千萬要平安。
在戰火中,每一刻都十分的漫長,在數次交火之後,終於等到那遲遲未來的日落。
「報告!在部隊的左翼,觀測到一、三連的行蹤。」
「通訊兵,立刻向他們打出旗號。」
空氣中,突然莫名震動,令人煩躁的嗡叫聲在耳邊響起。
「大尉小心!」
一陣白光在我眼角旁炸開,在失去意識的前幾秒,我看見通訊兵朝我撲了過來。
「佐藤少校,這裡有你的信!」還在神遊的我,被門外那有精神的報信聲拉回現實,我立刻就放下紙筆,直接往門口走去「謝謝妳加籐夫人,我馬上來。」,一開門加籐夫人便端了放滿豐盛早餐的餐盤走了進來。
「佐藤先生還沒吃早餐吧,我把早餐跟信一同放在桌上。」加籐夫人帶著十足家庭主婦的架勢,直接就把早餐放在桌上。
「這怎麼好意思。」慌亂之間,我不知道該把手擺在哪裡。
「沒事沒事,多虧少佐我們家才能知道外子在前線的消息呢。」加籐夫人一提到她的丈夫,幸福的表情就浮現在臉上,但我仍感覺到加藤夫人他的憂心。
「這是我份內的事情,應該的。」我拘謹地答道。
「不知道外子什麼時候能從羅莎莉亞回來呢,大戰不都結束了嗎?」
「我們軍人之所以存在,是為了防止戰爭再次發生,學長他還待在羅莎莉亞,是為了保護我們大和帝國所有人民的日常生活,現在羅莎莉亞的情勢尚未明朗,但我想在聯盟的介入下,很快就能平息紅軍所造成的動亂的。」我謹慎地選著用詞,希望能多少安撫一下加藤夫人。
「那真是太好了呢,我們家奈奈再過沒多久就要畢業了呢,希望外子在那之前就能趕快回國,如果可以的話,希望佐藤先生也一起來參加奈奈的畢業典禮呢。」
「這是我的榮幸。」我向夫人淺淺的鞠了個恭。
「佐藤先生也要多注意點,別一直忙在工作上,等等你的副官會來,我就直接讓他上來,還有佐藤先生早餐要記得吃,我還有事情,先離開了,晚上等奈奈回來,我會煮燉牛肉的,還請佐藤先生賞光呢。」
「一定一定,如此承蒙招待真的是令在下十分感激。」
「哈哈哈,佐藤先生你真是客氣呢。」語畢,夫人她便離開了。
門關起的剎那,我的思緒便漂回了羅莎莉亞。
「佐藤,這是你的升遷令,高層要你回國內一趟,沒意外的話,應該會調到南國去。」學長他沒點煙,但因為天冷,呼出來的白霧比菸還濃。
「等等,為什麼在這個時候?我們不是才來到羅莎莉亞沒多久嗎?這裡的戰況……」
「佐藤,冷靜一點。你跟我一樣都是佐官了,應該更加清楚軍人的天職是服從。」學長他從大衣中拿出了煙盒和火柴,慢條斯理地將菸給點上了。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,羅莎莉亞寒冷的空氣,刺痛著我的肺。
「你回國內的時候,幫我把大吾的消息帶回去給我內人吧。」
「學長……」
「不管怎麼樣,美代都有權知道她哥哥沒辦法回去了。」
我嘆了口氣,將思緒拉回現在,繼續將手邊的事情完成。
提起筆,將自己一路從瑯琊半島到覺羅國,最後到羅莎莉亞的種種寫進給母親的信中。我曾經有很多朋友,未來也會遇到新的朋友吧?但我仍舊想留住那些曾經一起奮鬥的夥伴……
遍地盛放的石蒜綿延無盡,灑滿星點的夜空被銀河跨越一分為二,流星劃過湛藍留下行進軌跡而又消逝。花叢之中,有位身著白色喪服的少年,面容也用白布遮掩起來。他靜靜地仰望著天,似是在欣賞這綺麗星空。
……那不是荻原家的臭小鬼嗎?為什麼會在這裡?
■■■■■■■從少年的身形和髮型辨認出他就是自家「少爺」。他嘆了口氣,原想前進卻發現自己的腳被什麼給絆住無法移動。
好像發現這一側發生了甚麼事情,少年將自己的臉轉向■■■■■■■。
然後,眼前的場景回到「自己」的房間。
清晨的陽光穿過窗櫺,灑落在正熟睡中的男子臉上。
「老師?」
見狀,荻原理人露出近似慈愛的微笑,伸手撥開遮掩住對方美顏的散亂髮絲。而被稱作老師的男子對他的行動毫無反應,依然閉著眼趴在那兒。
「已經早上了唷,老、師?」理人湊近對方耳邊,刻意壓低的磁性嗓音傳進對方的耳裡,這下他可終於醒了。
「真是的……就不會搖醒我就好嗎?」青年坐起身子,不耐煩地搔了搔頭。「你這臭小鬼……」他嘆了口氣,揉揉太陽穴。因為夢境的主角就在眼前,青年回想起方才的夢境。
反正不過就是人類腦袋在睡眠時會發生的危機模擬機制嘛,根本不需要特別注意。
■■■■■■■,無法用人類擁有的發聲器官傳述的,他的名字。身為寄居在這個身體裡的「偉大種族」,自然而然繼承了原主的姓名與身分——加賀美廣樹,專屬於荻原家的執事。
「嘿嘿、」理人因惡作劇成功不禁笑了出來,向廣樹遞出一張購物清單。「那麼今天也要麻煩您了,給。」
廣樹接下之後,隨意瞥過整張紙條說道:「這幾天就做這些簡單的東西?」
「畢竟現在才剛開學嘛,誰知道回來會不會很累呢?」
「如果只是學習那些東西也會累的話,我就錯看你了。」
「哎呀、老師真的很嚴格呢。」
就在這一來一往,荻原理人完成「叫老師起床」和「把購物清單交給老師」的任務,接下來就是吃完早餐出門上學了。
他收拾了一下書包內的物品,筆袋、筆記本、為了排解無聊的小說。畢竟是開學第一天,拿這些東西應該就夠了。荻原理人這麼想著,把書包放在自己的餐桌椅上。
這時,廣樹才慢慢從二樓慢慢走下來,看見餐桌上放好理人製作的完美早餐。「今天是馬鈴薯燉肉嗎?沒看你做過。」他打了個哈欠,坐到餐桌旁端詳桌上的菜色。此時的理人剛把貓飼料倒進王子的碗裡,順道摸摸王子柔順的白毛。
「剛好冰箱裡只剩這些食材就試著做做看了,應該不會很糟吧……」
「無妨,是你料理的就算有保證了吧。」
理人回到座位坐好後聽到這句便愣住了。好像被稱讚了但又好像沒有,單純陳述事實,還是對自己的廚藝有信心?以老師的歷練,肯定吃過世界上最美味的料理了吧?所以平常就沒有覺得很普通嗎?
「楞著幹甚麼?趕緊吃啊?不然要遲到了。」廣樹一臉無奈地將混著湯汁的米飯送入口中,看著突然甚麼動作都沒有的理人,不知道對方又突然想到甚麼。
「沒、沒事……我開動了。」總之回來再問問吧。他這麼想著,快速地把早餐處理掉。
「那麼,我出門了!」理人擦了擦嘴,揹好書包就往玄關走去。而廣樹則優雅地端著味噌湯和他告別:「路上小心。」
『疼……足疼的……』(痛……好痛……)
鏟入土裡的每一下,彷彿可以聽見那哀號的聲音,縈繞在耳。軟土深掘,本是讓亡者安息的無名墳頭,如今,被盜墓的賊人挖出了一窪盈著陰水的坑洞。
盜墓並不是我的工作,只是我的工作總和墳墓裡的東西脫不了關係;目的從來不是什麼墓中的財寶,所以我對這樣鬼鬼祟祟的作業,從來沒抱持過半點尋寶的興奮。
但這次不同。
「有、有矣……」(有、有了……)
從未如此戰慄的心跳正刺激著我的神經,挽起衣袖的雙手撥開蔭濕的土壤,挲摩在粗糙的棺木上。
「咳呵……咳呵呵呵呵……」
嗆鼻的氣味掀起我止不住的笑意,嗆醒的腦袋猶如還在睡夢之中,做著這久別重逢的幻夢。
但屍水的冰冷,是真的。
懷抱的重量,是真的。
落回水裡的腐敗,也是真的。
「好……真好……」(好……很好……)
讓懷裡的寶物浸濕貼身的白襯衫,我壓抑住過分急促的呼吸,自顧自地,把話灌進髮間的耳蝸裡:
「我轉來矣……閣等一下就好……すず(sír-jìr)……」(我回來了……再等我一下就好……)
「喀啷──喀啷──」
金屬碰撞的聲音不如鈴聲那般悅耳,形成的節奏緩步前行。
「喀啷──喀啷──」
被雲層籠罩成銀灰色的天空下,異常盛裝的身影出現在早晨的街市上。
和那些身著短衫、從台車上挑起一擔擔煤渣的工人不同,這裡的兩人就像是沒沾染到路面黃沙與車輿煤氣似地,漫步前進:
西式的陽傘遮掩著大半臉龐。隨著步伐搖曳,雪白的披肩如波浪擺盪,純黑鋪張出衣服主人纖細的流線,皮件與金屬綴飾下,斜面滾下的荷葉邊襯托著裙襬那朵層疊的梔子。從陽傘下伸出的纖白玉手,是從袖口的潔白花托裡,綻放的優雅花蕊。
若不是那些工人工作繁忙,我想,應該任誰也會想朝這邊多看一眼吧。
「喀啷──喀啷──」
拉著那小手的我配合著小手主人的步伐,為了盡量與那樣的她相襯,還沒穿慣的西米羅(註)伏貼在襯衫上,比我的形象還要堅毅挺拔;看著她領上的蝴蝶結,自己的領結應該不會過度誇張吧。
走過已然開張卻少有人客的店鋪,順著台車軌道,拐進往山裡的上坡路,開始聽到兒童嬉鬧的聲音時,目標已經不遠了。
到了。
帆山郡醉潭尋常小學校
在單邊圍牆盡頭停下腳步,面對著矮柱上刻著的十個大字,上課時間,從生鐵鑄成的校門朝裡頭望去,是孩童奔馳的操場,與醉潭常見的黑瓦歇山屋頂下、和洋折衷的宏偉校舍。
「就是遮。」(就是這裡。)
揉了揉牽著的小手,想讓她把眼前的景色看得更清楚一點;而我,朝鐵門的方向走近一步。
「不好意思──!」扯開了嗓子,有失禮儀地想引起操場上的注意,望見操場有個大人的身影走來,看來是挺有效的。
來人跨著乘馬袴拍打的步伐,快步走近校門口一邊的小門,髮際線上流下一道水痕,看上去可能已近中年。只見他用綁帶束起的寬袖裡一雙結實的手臂在鐵門後擺弄幾下,鐵門「喀」地應聲打開。
「請問有什麼事嗎?」帶上門後,男人朝這邊詢問。
「呃、不好意思,我是先前通過書信,前來請教編入事宜的,敝姓江。」
「啊、江先生!」他突然提高的聲量令我有些驚訝,但繼續聽下去,就不覺得奇怪了:「抱歉,自我介紹得晚了:我是教務主任奧野馬橋。」
「江墨槿,請多多指教。」
「請多多指教。」主任對這邊鞠躬回禮;注意到躲在我身後的女孩,他沒有抬起腰桿,而是將視線繼續擺在女孩身上:「那麼,想必您身邊的就是令妹──江……」
「棠硯。」把名字接續下去,我搖了搖被玉指勾住的手臂,示意她站出去一點:「海棠的棠、硯台的硯──江棠硯。」
一直低著頭的她,就像是含苞待放的花蕊一樣,看不清面目──但在禮貌上,這可讓我有點急了:
「すずり(註),共先生あいさつ(ai-sá-tsirh)。」(硯,跟老師打招呼。)
「……您好。」用和語吐露出這句話的雙唇怕生地抿在一起,圓滾滾的雙眸才從梳不整的髮絲下探出,瞳孔聚焦在奧野先生的面容上,才想起來要往旁邊一站、對師長鞠躬敬禮。
「哈哈,真有禮貌。」奧野先生的大手在棠硯頭上胡亂一搓,從那本來就難以梳整的頭髮上又搓出了幾根翹起的零亂:「在這邊不好說話,江先生,我們到辦公室裡聊吧。」
「現在有總督府推行的『和夜共學』,凡是能夠讀寫和語的孩子,我們都是不會拒絕的。」
在教務處的膨椅對坐下來,好客的奧野先生送上一盞清茶,我謝過之後啜飲了一小口,再將它擺回案上。
「時代不一樣了呢。」我隨口應道,想起自己還在學齡的那時,庄裡還是沒人上得了小學校的:「比起那些在路上亂跑的蒸汽機械,可能變化最大的是教育吧。」
「所言甚是──或許江先生您也有教育者的資質呢。」
「哈哈哈哈,主任您過獎了;我只是個只關心妹妹權益的自私之人罷了。」順著握住的手,我望向坐在身旁的妹妹──她的腰桿打得筆直,看著微微低頭的方向,一動也不動。
而就在這時,眼角餘光望見窗外有幾個小腦袋,正在窗台邊探頭探腦:
「那是誰啊?」「一動也不動的……」「是人偶嗎?」
──奧野先生應該也發現了,只是不打算阻止他們偷聽的樣子。
把注意力拉回桌上,我拿起清茶潤了潤喉:「不過,失學了四年,不知道能不能好好融入班級……」
「是叫做『硯』吧?」奧野先生話鋒一轉,突然朝棠硯那邊詢問;棠硯似乎還很緊張的樣子,點頭得有些緩慢。
「動了!」「動了動了!」「是那個啦!『Automaton』!」
窗外驚訝的聲音突然沸騰了起來,但奧野主任還是沒打算理會,繼續對棠硯問道:「硯醬,想要進我們學校讀書的話,要通過入學考試才行──有信心嗎?」
棠硯點頭,這次快了一些。
「哈哈哈,那很好。」環手大笑了幾聲的主任稱讚的說:「硯醬有這樣的信心,還有什麼好擔心的?」
「說的也是。」我搓搓棠硯翹起來的頭髮,對她的表現感到欣慰。
「但是!」奧野先生突然扯開了嗓門,把窗外的孩子嚇得都震了一下:「之後來上學的時候,可以別把硯醬打扮得這麼漂亮嗎?」
苦笑著上下打量女孩的裝扮,教務主任用拇指比了比窗外:
「穿這樣,活像個西洋的『Automaton』似的;會遭人誤會的。」
烏土媽統……那是什麼意思?
站在講台上,女孩捏著包袱上的綁結,面對台下四十多雙陌生的眼睛,即使表情沒有顯露出緊張,粉色大襟衫裡的身子早已緊繃僵硬;時不時,金屬製的雙腳也在紅海老茶色的女袴下抖出聲響來──而且那金屬音色每作一次響,棠硯的腰桿也多一分緊繃。
「這就是三年級在傳的『Automaton』?」「聽說入學考試考了滿分……」「真的假的……」「真的是機器嗎?」
背向的黑板上寫著女孩名字的三個大字──江棠硯;是工整得像印出來的美麗正楷。
「(硯醬……自我介紹……)」
一旁的女性輕聲提示,棠硯這才緩緩開口:
「……我叫做江棠硯,來自烘山角……請多多指教……」
什麼東西在燃燒。
紅蓮舔舐房裡的每樣東西,一個一個消失在火焰之中。窗外傳來陣陣的吶喊,他不知道窗外的人在生氣什麼,也不知道他們嘴中在叫罵著些什麼,更不懂他們為什麼要燒掉自己的家。
濃烈的煙霧進入自己的肺腔,惹得他一陣猛烈的咳嗽。被煙燻的視線早已因淚水而模糊,現在的他連看清路都很困難,更別提找出一條逃生路線了。
忽地,一股強健的力道將他抱起。
「爸爸……」
「有受傷嗎?」
「沒有……爸爸,外面那些人是誰?他們要做什麼?為什麼他們這麼生氣?」他看向抱起自己的男子提出疑問。
男人眼神複雜的看了他一眼,拍拍他的頭道:「沒事,這事爸爸晚點再跟你說。咱們先逃吧!現在保命比較重要。」
穿過房間的走廊,他們來到浴室。男人將他放下,在牆上摸索著,按下其中一塊磁磚,牆面向兩旁分開,露出一條漆黑的通道。
「來,走了,龍彥。快,」男人拉起他的手就要走。「在那些人找到我們之前。」
但他愣了一下沒有動作。
「龍彥?」
「可是,我明天和大家約好要出去玩的……」他有些猶疑的回應。
「沒時間了,那些事情之後再說。」男人瞥了眼外面,眼神越發焦急,反手用力將他拉進通道中。然後他扳動身旁的拉桿,通道的入口便自動闔上。
「喂!找到人沒?」
「都燒了房子,他們也沒地方躲了吧?」
「趁亂逃了?」
「不可能,四處都有人守著,都沒人看見他們。」
「嘖,再搜!把人給我找出來!」
漆黑的通道中,一大一小的身影在其中走著。
「爸爸,所以那些人是誰?」在這沉默中,他按耐不住地問了。
「沒什麼。」男人心不在焉的回應。「先出去了再說。」
「喔……」他有些失落,但心中的一片開始不安起來。從來沒有人這樣對他們,而且還把他們的家燒毀。
似乎是發覺他的不安,男人偏過頭輕聲安慰他:「沒事的喲!爸爸會陪在你旁邊的!」
「嗯,我知道了!」聽見這句話,他抬起頭,揚起笑容,樂觀的說:「因為爸爸很厲害啊!」
男人露出笑容,緊緊握住他的手,堅定地說道:「嗯,爸爸一定會保護龍彥的!」
他看著男人的眼睛,裡頭似乎流灩著些許的苦澀。他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,他只知道,父親很厲害,一定會保護他。
走出通道,沿著眼前的道路前行,他們走到鄰近市郊的地方。四周沒什麼人,倒是有著一片蓊鬱的樹林,可說是絕佳的遮蔽處。
「到這裡應該可以先鬆一口氣了。」男人看了看四周,確認沒人後,才扶著他輕輕坐下。「還好嗎?」
「……嗯,沒事。」他的心情雖然還沒恢復,但是仍揚起笑容看向男人。
「龍彥,接下來,爸爸要給你兩樣很重要的東西。你要記住,這兩樣東西是你千萬不能交給別人的。」
聽見男人少有的認真語氣,他也不禁正襟危坐。
「好的,爸爸。是什麼?」
男人將腰間上的刀卸下來,交到他的手中。「這是陸奧守吉行。它是我們坂本家祖傳的刀劍。這把刀就象徵著我們坂本家,是坂本一族的光榮和驕傲。你千萬不能讓它落入別人手中。」
他看著手中的刀,認真的點了點頭:「我知道了,爸爸。那還有一樣呢?」
「這個。」男人從口袋拉出一個藍色絹布的小袋子,將其打開,裡頭躺著一顆翠綠的寶石。在月光的照耀下,折射出亮光。他盯著看時,覺得有水波晃了一下。
「爸爸,這是……?」他不解的偏了偏頭。這石頭,在他看來也就漂亮了些,和他曾在街上櫥窗中看到的寶石相比,的確是遠勝一籌,除此之外就沒有特別之處了。他實在不解這顆漂亮的石頭重要在哪裡。
「這是守護我們家族的寶石。只要有這顆寶石在,我們在怎麼樣的困境都能突圍而出,一定能找到一條出路。」男人認真的說,眼神流露著堅定。
「那爸爸你拿著不是比較好嗎?為什麼給我?」他不解地看著寶石。照爸爸說的話,留在爸爸那裡不是更好嗎?他還只是個孩子,四處跑跳一下就掉了。
「因為你是家族的希望啊!從以前,你的祖父就是這樣說的。」男子將寶石收回帶中,放進他的衣襟。
「好了龍彥,聽好。從這裡一路走,千萬不要回頭,一直走就對了。過去後會看到一條溪,走過去後,再繼續往前,一直到一個小村莊。告訴人家你是原佐家的孩子。不要說出自己的真名,千萬不可以。」男人直直地望進他的眼底。
「那爸爸呢?」
「我會追上去的。」在鬆手之前,男人緊緊的抱住他,然後,輕推他的背,將他送進樹林。
直到那道矮小的身影消失在自己的視線後,男人緩緩地倚著一旁的大樹坐下。摸著交襟裡藏住的傷口,一陣刺骨的劇痛搔出流淌出來的殷紅。抬頭,男人認識那人的執拗,知道自己大概用不了多久就會被抓到了。
果然,沒多久,那人就出現了。
「坂本,把東西交給我,我可以饒你不死。」低沉的男聲說道。他穿著軍官的衣服,眼底的冷漠映著血的過往。
「呵,東西不在我這,我要如何給你?還有,你要的東西我不可能交上。要我的命,你就拿吧!反正依我這傷口,也不可能治了。」男人抬起頭,眼裡閃著堅定的光輝。再怎麼樣,他都要守住坂本家的東西!這是他們坂本一族的榮耀,豈能流落外人之手!
「真固執。」來人冷哼一聲。
此時傳來一陣沙沙聲。
「大人,我們搜遍了房子的殘骸,但什麼都沒發現。」一名穿著軍服的青年跑過來報告。
「我知道了。」軍官回頭,嚴厲的聲音問道:「這是最後一次機會,你真的要違逆『他』的旨意嗎?」
只見癱坐在地上的男人揚起自信的笑容:「呵,我說過,我不會讓你們拿到東西的。殺了我,你們也不會得到想要的答案。你們找不到的。」
樹林中,一道槍聲響起。